站在2025年的晨光里回望,烂柯山的风还带着当年熟悉的温度,一闭眼,记忆里校园的梧桐叶就沙沙响了——那是我青春星图里,最早亮起的一簇光斑。十九岁那年,我拖着印着碎花的布箱踏入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,林荫大道的梧桐树刚够两层楼高,5号楼与6号楼间,叶圣陶“千教万教,教人求真;千学万学,学做真人”的标牌被阳光晒得发亮,我攥着录取通知书的手心,还沾着老家稻壳的碎屑,像带着一颗未打磨的星子,跌进了这片校园。

如今二十年过去,我走过北上广深的玻璃幕墙,见过创投圈凌晨三点的灯火通明,却总在深夜被热咖啡的蒸汽晕开星图里的旧景:实验室金属切割机的嘶鸣是星子碰撞的声响;辩论赛场上晒暖的手卡是掌心托着的星光;烂柯山下足球场上,那件汗湿的白衬衫,像星图里最亮的那枚星,在风里轻轻晃。原来这座浙西的学府,早把青春的星子,一颗颗嵌进了我人生的轨迹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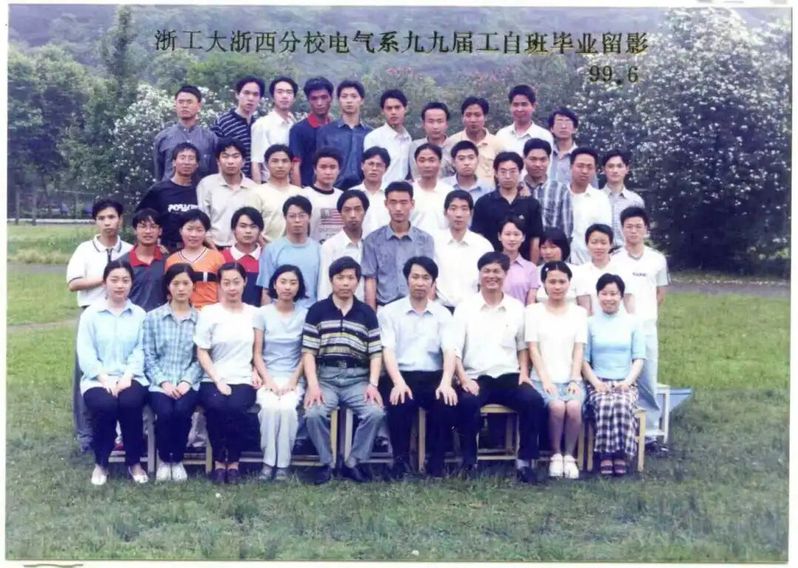
1996年的秋老虎格外肆虐,我们在闷热的实验室里第一次摸到游标卡尺。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传来时,朱小平老师正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机械制图:“工程人的眼里没有‘差不多’,0.01 毫米的误差,就是100%的失败。”那天我在绘图板前坐了整整四个小时,反复修改一条斜线的角度,直到台灯把图纸照出淡蓝色的光晕——这是我青春星图里,关于 “严谨”的第一颗星,后来成了我做决策的准则。如今在物联网项目路演现场,听见创业者用“大概”“可能”描述参数,我总会掏出笔记本列数据表格,年轻同事笑我“太较真”,我却想起那个深夜,朱老师敲着我的绘图板说“较真不是固执,是对结果的敬畏”,这话像星图里的指南星,帮我穿过无数商业迷雾。

母校从不是只教我们“计算”的地方。大二辩论赛,我们抽到 “科技发展是否会加剧道德滑坡” 的反方。为找论据,我和队友在图书馆泡了一周,还在操场草地围着收音机听时事评论。有天傍晚,我们把康德的“道德律”和自动控制理论写在同一张草稿纸,夕阳把字迹染成金色,风里飘着食堂的饭菜香——这帧画面,是星图里最暖的光。后来指导创业者路演,他们纠结“技术优先还是伦理优先”时,我总会想起那个黄昏:原来理性与感性从不是对立面,就像我在广播站念诗时,要反复调整语速,既要字正腔圆,又要情感落地。如今帮人改商业计划书,我总说“好项目要有数据,更要有温度”,那些在隔音间练出的表达力、辩论场养出的思辨力,是星图里的柔光,让我在冰冷的商业逻辑里,总能看见人心的暖。
最难忘1997年的冬夜,晚自习结束,宿舍楼海报栏前围满了人,白底黑字的通告写着“邓小平同志逝世”,我挤在人群里,眼泪突然涌上来。二十多年后,我投资的新能源项目断了资金链,团队成员主动降薪,没人抱怨,只说“再撑撑”,那一刻,冬夜的星光突然亮在眼前:原来青春里的家国情怀从不是口号,是困境里抱团的勇气。现在看项目,我总多问一句“能为国家解决什么问题”,有人说我“理想主义”,可他们不知道,那抹红早融进我的骨血,成了人生路上不变的坐标。
前阵子回母校,发现当年的梧桐树已长得参天,枝叶繁茂得能遮住整条主干道;学院里多了“国际友人”的面孔,他们和中国学生一起在实验室讨论,笑声清脆;1号实验楼的操作台换了新设备,但阳光透过玻璃落在操作台上的样子,和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。我站在窗外,看见学生们围着设备争论参数,有人拿着笔记本记录,有人用手指着屏幕讲解,恍惚间,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——那个在绘图板前熬夜的少年,那个在广播站念诗的青年,那个在足球场上奔跑的身影,原来从未离开。
那些在校园的日子,不是散落的回忆,是游标卡尺刻下的敬畏,是辩论手卡写满的思辨,是冬夜烛光映出的信念。母校是绘制星图的人,把工科的理性与人文的浪漫,一笔笔描进我的青春,让我在商业浪潮里守住初心,在岁月打磨中记得 “做人以真”。
就像钱江源头的水,朝着远方奔涌,而我的青春星图,永远亮着母校的光。它带着我,带着无数像我一样的学子,从浙西的校园出发,朝着更辽阔的未来,一路向前。


